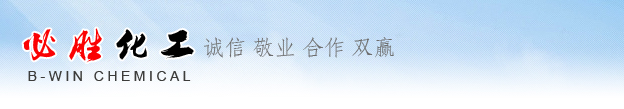你的位置: > 旅游資訊 >
塞罕壩:六女上壩,人生被造林改變
時間:2014-05-25 10:55來源:原創(chuàng) 作者:壩上的云 點擊:
次
40多年前的夏天,承德市二中6名女孩的一個決定曾經(jīng)轟動了整個城市:6名在城市里長大的女孩,放棄參加高考上大學的機會,毅然參加到塞罕壩植樹造林的隊伍中來。從此,這6名城市女
40多年前的夏天,承德市二中6名女孩的一個決定曾經(jīng)轟動了整個城市:6名在城市里長大的女孩,放棄參加高考上大學的機會,毅然參加到塞罕壩植樹造林的隊伍中來。從此,這6名城市女孩的命運緊緊地與塞罕壩那片荒涼的沙灘聯(lián)系了起來,她們的人生也因造林而產(chǎn)生了巨大的蛻變。
這個當時被稱為“壩上六女”的故事曾感動了很多人。如今,“壩上六女”已年過花甲,除其中的一位因病離世外,其他幾位都在享受著恬淡而舒適的退休生活。然而,在她們記憶的最深處,還是塞罕壩的那片土地,那片樹林……
■決定上壩
43年過去了,“六女上壩”中的倡議者陳彥嫻早已是塞罕壩機械林場退休老干部中的一員,打門球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
8月6日下午,記者在圍場縣城塞罕壩機械林場的老干部活動中心見到陳彥嫻時,60多歲的陳彥嫻開朗、樂觀,她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的每一個細節(jié),談起與塞罕壩相關(guān)的事情,激動的表情中還有一些振奮。
陳彥嫻讀高中的那陣子,正值中央號召知識青年下鄉(xiāng)鍛煉,邢燕子是大家學習的楷模。“當時,一個班的女生住一個宿舍,20多個人擠一個大通鋪,稍微有點風吹草動,女生們總喜歡嘰嘰喳喳說個不停。在邢燕子的鼓舞下,大家也都有那么一股沖動和熱情,希望下鄉(xiāng)鍛煉,好好干一番事業(yè)。這個話題成為我們私下里談論最多的話題。”1964年夏天,在她們即將高中畢業(yè)之際,究竟是參加高考上大學還是下鄉(xiāng)鍛煉,顯得更為急迫起來。
就在這時,陳彥嫻記起了住在家對門的劉文仕在塞罕壩工作,還是塞罕壩機械林場場長,曾經(jīng)聽說過,塞罕壩機械林場剛成立不久,機械化造林需要人手。
隨后,陳彥嫻就向大家發(fā)布這個信息。得知這一信息后,大家都很興奮。很快,班級里包括陳彥嫻在內(nèi),就有6人響應要去塞罕壩機械林場工作了,分別是甄瑞林、王晚霞、史德榮、李如意、王桂珍。
幾個女孩子商量后決定,馬上給劉文仕場長寫封信。說干就干,陳彥嫻代表六位女生寫信,信中表達了她們想到壩上干一番事業(yè)的決心。一個月后,也就是5月份,陳彥嫻她們幾人收到了來自塞罕壩機械林場的回信。信中表示,場里十分歡迎她們?nèi)スぷ鳌?/div>
“也就是這時候,我們才把去壩上的想法告訴學校和家長,學校很支持,還特意召開座談會表示肯定。家長的反應就不同了,大多數(shù)家長都不同意我們放棄高考。但我們都鐵了心一定要去壩上,家長做了很多工作都是徒勞。”陳彥嫻說,就這樣,在青春夢想的美好憧憬中,6名女孩沒有參加高考,等待著去壩上轟轟烈烈地大干一場。
■顛簸上壩
1964年8月21日,塞罕壩機械林場的汽車到承德市來接“六女”上壩了。
“汽車是一輛大卡車,還是敞篷的。坐上車的那一刻,別提我們有多興奮了!可是,越走越荒涼,越走人煙越稀少。對于第一次走出承德市的我們來說,心揪得緊緊的,不知道將要去的塞罕壩究 竟是怎樣一番模樣。”陳彥嫻說,那時候從承德到圍場還沒有公路,都是土路。走到隆化縣時,由于下雨沖毀了一座橋梁,沒路可走了,只好寄宿在一不相識的老鄉(xiāng)家里。
第二天早上繼續(xù)趕路,直到下午3時才到達圍場縣城。開車的司機告知天黑前上不了壩,又住了下來。“當時的圍場縣城只有一條街,街上到處是牲畜的糞便,由于剛下過雨,地面上的水與糞便摻和在一起,氣味很難聞。街道兩邊是十分低矮的土房,好像一伸胳膊就可以夠到屋檐。”
陳彥嫻說,雖然當時的承德市區(qū)建設(shè)得沒有現(xiàn)在好,圍場縣城的那番模樣,是她們幾個第一次走出家門的女孩絕對沒有想到的。當天晚上住在一家叫“三分店”的旅店里,“由于很多人靠牲畜拉的大車行遠路,旅店也就成了驛站,旅店里不僅住了人,還有牲畜。我現(xiàn)在還記得,旅店里的被子很黑,我們幾個和衣而睡,等待著第二天的啟程。”
23日一早,陳彥嫻等六個女生乘坐的大卡車又上路了。“這時,路上更荒涼了,幾乎沒有行人,幾個女孩早已沒有先前的“嘰嘰喳喳”,沉默了。司機師傅一直鼓勵說,‘快到了,快到了’,然而,就是到不了壩上。下午3點多才到達塞罕壩機械林場總場,當時綿延無垠的壩上還到處是一片荒蕪的山嶺,看不到多少樹木。”
陳彥嫻說,她們乘坐的大卡車到達御道口時,看到了在城市里沒有看到過的藍天、白云,草地上隨風搖蕩綠草。看到這樣美麗的風景,大家的興致一下子又來了,又開始說笑,還禁不住唱了起來。偶爾看見她們的壩上小孩兒,還以為是“馬戲團”的來了。
到壩上后,機械林場的領(lǐng)導十分重視,親自陪著上壩的“六女”吃了第一頓飯。“當晚吃的是烙餅,原料是本地產(chǎn)的又黑又粘的莜面,有一種難以下咽的感覺。”陳彥嫻后來才知道,那已經(jīng)是拿出當時最好的飯來款待她們了,平時根本吃不到烙餅。
■壩上人生
“六女”上壩后,全部被分到了千層板林場的苗圃中工作。
“在我們的夢想中,上壩后就可以開上神氣的拖拉機或其他大機器,進行機械化造林了。令人沒有想到的是,我們在苗圃的第一件工作是倒大糞,不僅要克服難聞氣味的侵襲,還必須跟上大家的節(jié)奏,流水作業(yè),轉(zhuǎn)著圈兒地倒,不停走動。一天下來,我們幾個腰酸腿痛。”
陳彥嫻說,晚上談起第一天的工作,六個女孩都不服氣,大家商量后一致認為,別人怎么干,她們就怎么干,不信干不好。幾天下來,在“六女”的努力堅持中,大家也改變了對她們的看法。
事實上,自從她們上壩那天起,她們幾個人的命運就緊緊地與塞罕壩那片荒蕪的山嶺聯(lián)系起來。從此,這六名來自城市女孩的人生軌跡,也由此發(fā)生了巨大的改變。在這里,她們不僅要克服惡劣的氣候條件,還要忍受飲食上的不適應,以及高強度勞動對身體的挑戰(zhàn)……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她們都認為小米飯和土豆是最好的飯食,每每吃土豆時,她們就買很多,放著慢慢吃,時間長了,人們都叫她們“土豆”。
“六女”上壩后不久,塞罕壩的冬季就來臨了。“記得是陰歷八月十五左右,我們在一個大工棚里選苗。
外面下著雪,棚內(nèi)十分陰冷,而苗子都在水中。一坐就是一天,又冷又濕,手都麻木了。”在陳彥嫻的記憶中,不管外界條件如何惡劣,她們幾個始終沒有抱怨過什么,而是努力地克服困難,總希望干啥也不比別人差。
“第二年冬天的上山伐樹中,我們與男子一樣,在沒過膝蓋的大雪中伐樹,再拿繩子捆好,用肩膀拉著從山上向下滑。在凜冽的‘白毛風’中,我們的臉、耳朵都凍得起泡了。在這種情況下,越是站著越冷,所以大家只能干活,比著干,看誰干得好、干得多。”陳說,在上山伐樹的那一個多月磨煉,讓領(lǐng)導都十分佩服她們這幾個來自城市的女孩。
1964年春節(jié)放假后,也是她們幾個女孩第一次回家。回家前,大家都買壩上冬天要穿的“氈疙瘩”,穿上厚厚的棉襖,帶上厚厚的皮帽子,再次坐上了敞篷車,一路奔波回到了承德。“下車的一剎那,市民們還以為是‘外星人’來了,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裝扮。”
■無怨無悔
坐在位于林場縣城的塞罕壩機械林場老干部活動中心,陳彥嫻老人講述起當年的那一切,始終面帶笑容。她說,雖然經(jīng)受了很多艱苦和磨難,但從來沒有后悔過當初的選擇。“現(xiàn)在,每每看到自己親手栽下的樹苗長起來,還長成了一片林子,那種幸福和自豪感,是很難用語言表達的。雖然退休離開了那片林子,但看到一車車的木頭從壩上拉下來,自己曾經(jīng)的艱辛和付出十分值得,這種成就感是其他任何東西都替代不了的……”
1976年,陳彥嫻的母親不僅給她找好了接收單位,還親自來塞罕壩做她的工作,希望她調(diào)回承德,過相對安定和舒適的生活。經(jīng)過再三思考,陳彥嫻還是放棄了調(diào)回承德的機會,留在了塞罕壩那片正在茁壯成長的樹林。
陳彥嫻說,高中畢業(yè)前夕,由于她自己是一名閑不住的“活躍分子”,喜歡參加籃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等各種體育運動,經(jīng)常參加省內(nèi)、甚至是全國的比賽,尤其是滑冰,長短道速滑、花樣滑冰都還不錯。“由于很多時間花費在體育運動上,我的學習成績說不上特別好。而李如意、王桂珍、史德榮等幾位就不一樣了,她們絕對是學習成績十分優(yōu)異的學生,參加高考上大學沒有任何問題。”
在塞罕壩工作多年后,由于種種原因,大家也各奔東西了。目前,甄瑞林在山東,史德榮在武漢,李如意在張家口,王晚霞在承德,王桂珍則因病已經(jīng)去世。
陳彥嫻說,到目前為止,已經(jīng)有10多年沒有了李如意的消息。通過多方聯(lián)系,“六女”中的四人今年7月中旬在承德相聚了,甄瑞林、來自武漢的史德榮,以及在承德的王晚霞和陳彥嫻,4位60歲老人分別數(shù)十年后重新見面,你一句我一句的,仿佛回到了從前。但大家談論最多的還是在塞罕壩的那段歲月,關(guān)于塞罕壩的樹林,關(guān)于塞罕壩的點點滴滴。說起那段歲月,大家的感覺十分一致:無怨無悔!
在陳彥嫻看來,正是他們那一代人的“無怨無悔”,才有了今天綿延百萬畝的林海,才有了林場的今天。
(責任編輯:壩上的云)
上一篇:塞罕壩的綠色奇跡
下一篇:克旗達里湖華子魚回游
相關(guān)新聞
- (20-03-24)
- (20-03-23)
- (20-02-27)
- (20-02-24)
- (17-06-04)
- (17-06-04)
- (17-04-07)
- (17-04-07)